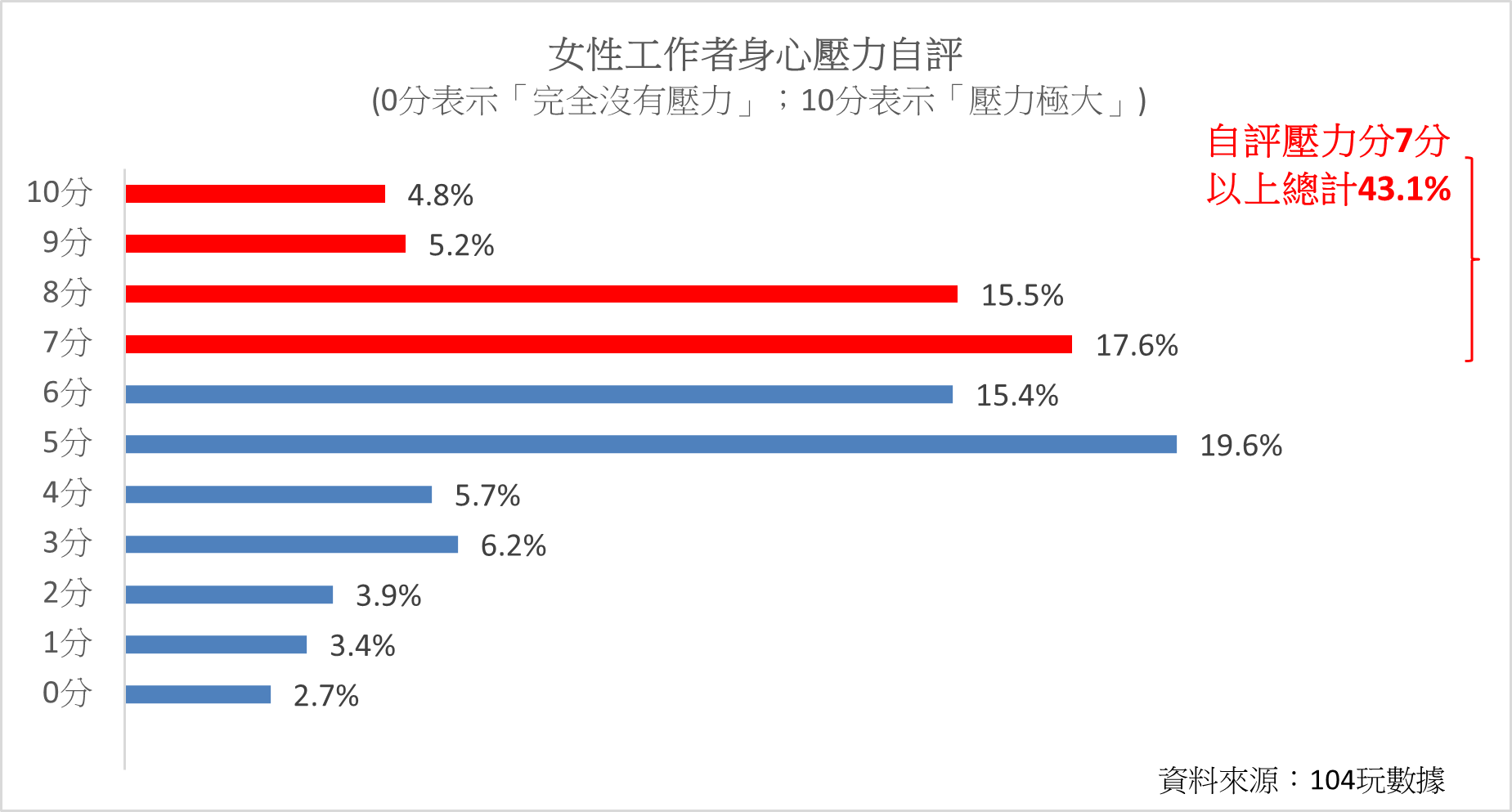幾年前,身為大學教授的我不是把早晨時光用來備課,而是賴床幾小時,重複看著英國流行歌手Peter Gabriel在1986年和Kate Bush對唱〈Don’t Give Up〉的影片。在影片中,2位歌手擁抱在一起6分鐘,背景是一段日蝕。
Gabriel以豐富的情感傳唱出絕望和寂寥,呼應著我內心的獨白;Bush滿懷慈悲的反覆唱著歌名的幾個字,保證這些苦難都會過去,但我不管聽幾次都覺得這些字眼很不真實。
我的第一堂課在下午2點;我會勉強準時到、勉強準備好,一上完課就回家去。晚上我就吃冰淇淋、喝麥芽釀造的高濃度啤酒——通常會加在一起,做成漂浮冰淇淋。我胖了30磅。
以任何客觀標準來看,我擁有一個非常棒的工作。我運用高度的技術和訓練,從事自己擅長的事:教授宗教學、倫理學及神學。我的同事們聰明又和善,我的薪資令生活無虞,福利更是沒話說。我有很大的自主權可以決定如何教課、進行研究計畫,而且我拿到終身教職,擁有的職業保障是學術圈外不曾聽聞的,在學術圈內也日漸少有。
但我仍然很痛苦,我想放棄。我職業倦怠了。
什麼是職業倦怠?其實是富裕國家整體的工作文化
當時,我以為這只是我自己有問題。我怎麼會討厭這麼好的工作?
我後來才明白,職業倦怠的問題,遠遠大過一個工作者的絕望。美國、加拿大和其他富裕國家的人民,已經建造出一整個環繞著工作的職業倦怠文化。個人不該為職業倦怠受責怪,但一定會感受到其負面影響。
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拉赫(Christina Maslach)看出職業倦怠有3種特點:
- 身心枯竭。
- 憤世嫉俗(有時稱為非人性化)。
- 感覺無效能或成就變小。
在這些時候,你就是職業倦怠了:當你經常耗盡氣力(身心枯竭),當你把客戶或學生看成問題而非你要幫助的人(憤世嫉俗),當你感覺在工作上一事無成(毫無效能)。
我對這3點都有強烈的感受。早上醒來就覺得很累,很畏懼眼前的工作;要拚命遏制那些毫不在乎的學生及行政人員帶給我的挫折感;認為自己的努力付出和才能,全都是白費工夫。
學生根本不想學習時,我的職業生涯形同廢物。
我的職業倦怠經驗起伏變動了好幾年,後來才變成固定的情況。我逐漸產生憤世嫉俗和無效能感,嚴重的身心枯竭再後來才有。
通常,我每個學期會教授4門通識教育課。學生們就在課程評鑑中表達自己的憤恨,「這麼沒意義的課,給分太嚴又太愛找麻煩。」這是典型的評語。
為了得到專業上的滿足,我也把時間投注在這份工作的其他方面:委員會、研討會、發表論文,卻造成負面的影響。
我寫了一段話給自己:「這些事情令我身心俱疲。這不是知性上的挑戰(是挑戰,卻非知性上的),也不會真的有回報,因為大部分學生都不像有從中獲益,而少數有獲益的學生也沒有向我表達絲毫謝意。」
括號裡的那句話說到,教書並不是一種知性上的挑戰,突然引起我的注意,它告訴我,我投入這份工作所期待的是一件事、得到的卻是另一件事。
職業倦怠的起點:對工作的理想和現實,有巨大落差
我想過著「我想像的教授生活」。我投入學術界,心裡以為自己會變成文藝共和國的公民。但其實這依然只是一份工作,有官僚體制的繁文縟節和工作時程,以及5點下班前需要完成的無聊工作。
而且學生沒有把學習視為一種崇高的知性追求,他們認為教育是成為會計師、運動防護員或老師的一個途徑。我不怪他們,但我忍不住期待他們跟我一樣。
我們對工作的理想與工作的現實之間有一道鴻溝,這就是職業倦怠的起始點。當我們在工作中實際上做的事達不到我們原本的希望,就會職業倦怠。
那些理想和期望不只是個人的,也是文化上的。在富裕國家的文化中,我們想從工作得到的不只是薪水,還想要尊嚴、想要長大成熟,甚至想要一些超然的目的。
我愛死當大學教授之前的工作:停車場收費員
當大學教授之前,我擔任停車場的工作人員。我當時剛拿到博士學位,找不到學術界的工作。但我認識幾個在大學對面路邊停車場工作的人,他們把我介紹給老闆,不久後,我就在那飽經日曬雨淋的小亭子裡收費。我每天坐在教授的富豪和寶馬轎車駕駛座上,滿心期盼自己能像他們一樣。
我愛死這個工作了,輕鬆又好玩。老闆會關心員工,對我們很好,他知道這份工作並不是我們生活的全部。
我的同事都是天資聰穎的大學生和研究生,其中有幾個人身上有刺青,騎著單速腳踏車,在收費亭裡播放晦澀難懂的硬蕊龐克搖滾樂曲。
我在停車場工作的那一年,愛上了一個同樣處在生涯過渡期的女孩子,她會帶咖啡和甜點來,幫助我撐過夜班的時間。現在她是我的妻子。
我從事社會地位低的工作得到的快樂,與終身教職的學術界職位帶給我的痛苦,二者的對比指出了終結職業倦怠文化的一條明路。
擁有夢幻職業後卻不快樂,問題出在哪?如何終結職場倦怠?
我期望成為大學教授,會使我成為一個完整的人,不只是個勞動者;我期望大學教授是我完整的身分認同,是我人生的天職召命。當然,這份工作並沒有達到那些期望,我辛苦勞碌多年,後來因為失望和徒勞無益的嚴重程度超過我所能承受,於是我辭職了。
相反的,我當停車場工作人員時,對工作沒有什麼崇高的理想,只當成一種不費力賺到房租的方法。
我沒打算「積極投入」這份工作。如果你是停車場服務員,就不會有體驗到「心流」的可能。在小亭子裡收錢,不會有漸進式的挑戰,沒有人會做得越來越好。唯一會給你回饋的人,就是試圖規避停車費而怒氣沖沖的駕駛人。
我做那份工作時,從來沒有沉浸其中而忘記吃飯。這份工作絲毫沒有促使人全神貫注於某個任務,要令工作有成效、讓勞動者充分實現理想,非常完美。
我深信,沒有積極投入工作,正是我在停車場當服務員那一年會如此快樂的原因。這項工作抗拒任何要在道德上或靈性上有意義的努力,它沒有承諾會給人尊嚴、品格的成長或目的感,它從來沒有提供幸福生活的可能性。
因為我無法在工作本身中實現自我,我就得從別處去找,而我也找到了:在寫作中、友誼中、愛情中找到。
我要很小心,不要從可能是自己的獨有經驗,過度引申出關於工作本身的任何結論。但我擔任教授及停車場服務員的經驗,確實符合我的研究帶給我的職業倦怠模型,也就是,我們帶進工作的文化理想,對於職業倦怠如何侵襲我們,具有主要的影響。
有太多勞動者處在職業倦怠的危險中。我們自1970年代以來,在工作中受到危害的事實,與太過高尚的工作理想同時產生。我們的理想和工作經驗之間,鴻溝實在太大,令我們無法承受。
意思就是,如果你想終止職業倦怠的流行病,就需要縮小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;方法是改善工作條件,並降低理想。
*本文摘自游擊文化《終結職業倦怠:工作為何將人榨乾,又該如何建造更優質的生活?》

《終結職業倦怠:工作為何將人榨乾,又該如何建造更優質的生活?》
作者:喬納森·馬萊西克(Jonathan Malesic)
譯者:劉思潔
出版社:游擊文化
出版日期:2024/04/02
作者簡介
喬納森·馬萊西克(Jonathan Malesic)
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宗教學博士,曾在大學任教十多年,也當過壽司師傅和停車場服務員。現為自由撰稿人,文章發表於《紐約時報》(The New York Times)、《新共和》(The New Republic)、《大西洋》(The Atlantic)、《華盛頓郵報》(The Washington Post)、《公益》(Commonweal)等媒體刊物。作品曾由《最佳美國散文集》(Best American Essays)和《最佳美國飲食書寫》(Best American Food Writing)認定為值得注目的散文,並獲得手推車獎(Pushcart Prize)文選的特別表彰。最新著作《終結職業倦怠》(The End of Burnout)翻譯十國語言,獲Amazon和Next Big Idea Club評選為2022年度好書。
責任編輯:倪旻勤
核稿編輯:陳瑋鴻